当藏北高原的风掠过雪山之巅、拂过湖泊镜面、漫过草原腹地,那些被阳光镀上金边的雪峰、随光影变幻色彩的湖泊、在旷野上灵动奔跑的生灵,共同勾勒出羌塘高原的壮美画卷。这片被称为“尼玛”(藏语,意为太阳)的土地,正是援藏干部孙鹏笔下《云朵上的旷野》的叙事核心。全书铺展三重书写维度:对高原自然生灵的深情凝望,对藏北历史文化的温柔叩问,对各民族跨越山海的联结与成长的真实记录。
作为中央单位第十批援藏干部,孙鹏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尼玛县挂职期间,既是俯身为当地群众解决饮水、供电等实际难题的实践者,也是蹲守校园为孩子们搭建阅读角、传递书香的志愿者。他以“在场者”的身份深入当地生活肌理——跟着牧民赶羊,听老人讲过往故事,又以儿童文学创作者的细腻敏锐,将高海拔的艰苦、生命的坚韧、文化的厚重,转化为一个个可触摸、有温度的文字片段。
书中对高原自然的叙述,充满鲜活的“在场感”。作者笔下的湖泊各有性情:“色林错像块沉静的蔚蓝宝石,当惹雍错却调皮得很,清晨是奶油色,正午变孔雀蓝,黄昏又成了橘红色,湖面倒映着雪山时,仿佛把天空裁了一块铺在地上,还藏着‘冬天不睡春天睡’的脾气。”这些拟人化的表达,既展现了藏北湖泊的视觉壮美,也暗合高原万物有灵的生态观。
作者对无人区生灵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藏羚羊‘迎迎’的雪地婚礼要持续21天,公羊们用犄角划出领地,低头喷气时鼻息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藏野驴‘江江’既是优雅的‘模特’,也是会挖井的‘荒原工程师’,用蹄子刨出的水坑边缘结着薄冰,却能让整个兽群解渴”……作者没有将动物简单归为“景观”,而是称其为高原的“居民”,通过“婚礼”“挖井”等拟人化行为,揭示旷野从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共生、彼此滋养的家园。
在自然的怀抱里,藏北的历史与文化更显厚重。当惹雍错湖畔的文布南村,住着古象雄王国的后裔。82岁的次仁爷爷常坐在玛尼堆旁,用布满皱纹的手比划着讲述王国旧事:“从前的王骑着白牦牛,宫殿金顶能照亮半个湖。”村里的建筑藏着古人的智慧。村民用“公石头”(方石)和“母石头”(圆石)交替垒砌石屋,用混着牦牛骨髓的泥浆黏合,既稳固又保暖。更巧妙的是,石屋地下的“地道战”网络,原本是抵御侵袭的防御工事,如今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乐园,傍晚常有小孩举着松明子在隧道呼喊:“我是象雄勇士!”
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承同样动人。藏北的孔雀舞由老爷爷演绎,一抬手似要划破风雪,一跺脚能震落屋顶积雪,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祖辈传下的刚劲;而盐的故事更是感人,从前小伙子们赶着绵羊驮盐换粮,盐袋磨破了绵羊的皮肉就垫上羊毛继续赶路。老人们说“盐是大地的结晶,不能沾眼泪”,那“不能沾眼泪”的叮嘱,不仅有对自然馈赠的敬畏,更藏着日子再苦也不能低头的骨气。
自然与文化之外,书中最暖的篇章,是人与人之间跨越民族的联结与成长。援藏老师崔卓从山西来到尼玛,把古诗词编进锅庄舞,“床前明月光”与孩子们的舞步交织融合;她一留就是一辈子,黑板上的粉笔字写了又擦,粉笔灰混着高原风沙融进土墙。
这样的温暖藏在无数细节里:援藏干部带着技术人员修光伏电站时,藏族老乡端来滚烫的酥油茶,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太阳也能当柴火,真好”;北京阿姨寄来会跑的小汽车玩具,字条上写着“要像草原小草一样长,长大了去北京看天安门”。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空洞的口号,这些故事里,援藏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解决难题,援藏省市的孩子与藏北的孩子彼此牵挂,各民族的情感在日常相处中慢慢沉淀,成为高海拔地区最动人的温度。
《云朵上的旷野》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打破纪实与文学的边界,用巧妙的艺术手法让藏北高原“活”了起来。真实是它的根基,作者作为援藏干部,以“在场者”的视角记录一切——见过藏羚羊在雪地里追逐的憨态,公羊们用前腿拍打胸口示威,发出“咚咚”的闷响;亲身爬过岩羊走过的陡峭山壁,脚下的碎石哗啦啦往下掉,才明白什么叫“如履薄冰”。
书中没有“滤镜”,既写高原的壮美,也不回避它的严酷——尼玛县“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10月就飘雪,5月还结冰;树要在温室里才能存活,孩子们跑几步就会喘,脸上的“高原红”是紫外线留下的印记。这种不粉饰的真实,让每个故事都像从高原土里长出来的,扎实而有力量。
与此同时,诗意是它的翅膀。作者擅长用生动的细节让文字“发光”:绿头鸭的脑袋“像墨玉雕成的挂件”,游动时脖子一伸一缩像在点头,划开的水波里闪着细碎的光;藏原羚跑起来,屁股上的心形白毛“像挂着个洁白的桃心”,远远望去像草原上跳动的星星。
《云朵上的旷野》像是一封来自高原的“信笺”。它让我们知道,海拔4800米的高原之上,有我们不熟悉的生活,却有和我们一样的欢笑与成长;旷野或许遥远,但万物的联结、人心的温暖,从来都触手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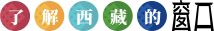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