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封建社会最残酷的奴役形式。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政治压迫、经济盘剥、精神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百万农奴挣扎在极其黑暗、极端贫困、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西藏地方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长期遭受压迫的西藏百万农奴也强烈要求进行改革。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特殊情况,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给西藏上层留出主动进行改革的时间。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妄想维持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全面发动了武装叛乱。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由此,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了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跨越,不仅实现了从旧西藏“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到今日“雪域之巅的幸福家园”的彻底蜕变,同时也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伟大征程。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终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根本矛盾使然,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次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与西欧、俄国等地相比,西藏民主改革的彻底性,表现在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生产关系、文化思想等维度。
政治制度的革命性重构:从“专制统治”到“人民民主”的划时代变革
西藏农奴制,是从吐蕃时期的奴隶制演化而来,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是20世纪中叶最野蛮、最落后的制度。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原因并不在于地理环境的封闭,而是在于高度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在这一制度的运行中,农奴主阶级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实现对广大农奴的专制统治,形成了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农奴主阶级统治的形式。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曾指出,政教合一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
民主改革后,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被彻底终结,百万农奴翻身作了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选举产生西藏各级人民政权。大批农奴和奴隶出身的积极分子迅速成长,成为优秀的民族干部。通过踊跃参与政权代表的选举,人民群众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全面建立并不断完善,百万农奴不仅获得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还获得了公民的各项权利。
阶级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从“人身依附”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划时代变革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粗暴践踏人的尊严,广大农奴除了终身劳作外,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完全被异化为“会说话的工具”。在这一制度下,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生为农奴的命运。农奴被农奴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赌博和交换。同时,为了镇压广大农奴的反抗、维护其自身利益,旧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制定了残酷的“法典”。在旧西藏通行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无法通过任何途径改变身份。同时,在这一黑暗制度和法典的禁锢下,农奴极端缺乏民主权利,没有任何自卫和反抗的可能,否则将面临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等野蛮的刑罚。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扼杀西藏广大人民民主权利的专制制度,是旧西藏广大人民黑暗生活的罪恶根源。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彻底瓦解了阶级压迫体系,百万农奴从此翻身解放。人不再分为三六九等,每个人不分贫富、地位和文化程度,从人格上一律平等;同时,人民群众有了劳动的自由、流动的自由、自愿交往和婚姻自主的自由。被压迫千百年的农奴,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第一次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生产关系的本质性变革:从“私有剥削”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划时代变革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其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并通过超经济的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广大农奴被迫处于服从的地位,终年劳动却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其次表现在超经济剥削的运行机制。西藏农奴主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和对农奴人身的超经济强制占有。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此外,农奴主还通过发放高利贷、强迫摊派借贷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了对农奴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束缚。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之下,旧西藏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牧业停滞在原始生产方式上,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同时,由于旧西藏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各种灾害造成大面积饥荒和大规模人畜死亡的情况频发。在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地,到处可见乞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废除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彻底打碎了西藏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完成了由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跨越,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劳动主体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热情。百万农奴翻身作了主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不仅可以在属于自己的耕地和牧场中进行劳动和收获,还可以取得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由支配的权利。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广大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此开始西藏人民才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
思想文化的系统性重塑:从“精神钳制”到“文化繁荣”的划时代变革
旧西藏的文化生态,是由具有文化专制、文化压迫和文化剥削属性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所决定的。政教合一体制之下,少数人不仅掌握着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军队、粮食、生产工具等主要社会资源,而且通过佛教宿命论和轮回转世思想,在精神上恐吓和麻醉各族人民,使他们不敢反抗。农奴被灌输“轮回转世”思想,认为今生受苦是前世罪孽,甘愿忍受剥削。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写道:“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段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构成僧俗一体的联合专制体系,成为广大农奴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枷锁。在某种程度上说,利用宗教信仰实现精神钳制比世俗的压迫统治更加残酷。同时,旧西藏的百万农奴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夺、被奴役状态,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毫无保证,更谈不上文化教育权利。直到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正规学校,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操控在统治者手中。农奴主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凡与“三大领主”的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1959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逐步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迈入了崭新的时代。西藏文化从此结束了为少数上层封建僧侣贵族所垄断的历史,成为西藏全体人民继承和发展的共同文化遗产。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为满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全体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
(执笔:黄慧,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西藏自治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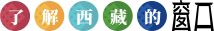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2号